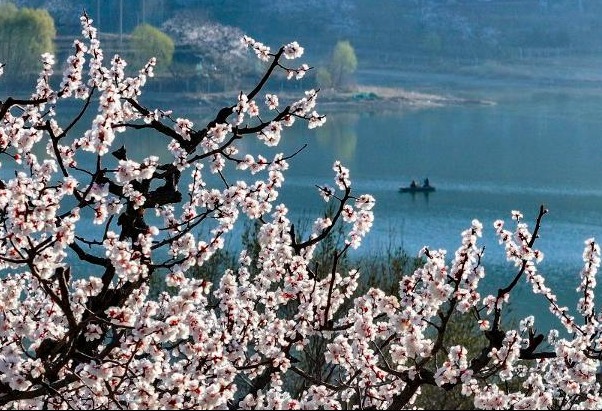大众网
冯沅君古代戏曲研究的当代价值
周爱华
冯沅君先生(1900-1974)是我国著名作家、古典文学史家,她一生治学严谨,在学界影响广远。冯先生的古代戏曲研究是其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古剧四考》《辑本题记》《金院本补说》《南戏拾遗》(与陆侃如合编)等。此外,冯先生去世以后,其弟子厦门大学黄祖良教授将其讲稿《中国古代戏剧专题研究》进行整理,分为三期发表于《艺术百家》杂志。《古剧说汇》汇集了冯先生从1935年以后十年内所写的关于古代戏剧的考证文章,这也是本文主要关注对象。
与先生其他成果的关注度、传播度相比,其古代戏曲研究成果在学界受到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李玫在《古代戏曲研究风尚得失谈》中曾论及古代戏曲作品少人问津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体裁中,从文本阅读的角度看,古代戏曲作品可以说是与今天的读者最为疏离的一种。它不像古代诗词、古文和古代小说、甚至古代散曲那样,今天或多或少仍有读者,尤其是古代诗词,今天仍不乏热爱者甚或习作者,而古代戏曲作品则除了研究者,少有人问津。”[1]这句话同样可以解释古代戏曲相关研究成果不被关注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冯先生的研究成果犹显珍贵。在提倡文化繁荣、戏曲振兴的今天,尤其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学术浮躁期之后,重新阅读冯先生当年的戏曲研究成果,重新学习其朴学、史学与美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厘定古代戏曲相关概念,梳理戏曲发展历史,倡导扎实朴实的学术风气,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冯沅君古代戏曲研究的学术价值
冯先生博览群书,治学谨严,方法灵活,创获丰硕,在民国时期古代戏曲研究队伍中地位举足轻重。纵观其研究成果,其研究类型大略可分为文献辑佚、概念考释、史论研究,其治学格局大致可概括为辑佚—研读—考证。她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基础上,结合大量古代文献,将中国戏曲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她在研究过程中敢于质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很多古代戏曲概念经过她的疏证和补充而更加清晰,至今仍被学界广泛继承,充分体现了它的当代学术价值。下面大体罗列一二。
1.关于“诸宫调”的研究
诸宫调是戏曲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始于汴京孔三传,金董解元的《西厢》为其仅有的代表作。《碧鸡漫志》《梦粱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相关文献都有记载。陶宗元《辍耕录》谓:“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时代未远,犹罕有人能解之。”[2]大概是流传时间短、地域小的原因,后人竟然不能辨识。沈德符《野获编》认为其乃“金人院本模范”[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做了初步考证,否定了这一看法,将其确定为诸宫调,认为“诸宫调者,小说之支流,而被之以乐曲者也”[4]。他引用并以《太平赚》《定风波》相关词赋中均含有“诸宫调”一词证明其观点。至于体例,“求之古曲,无一相似。独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所选者,大致相同。”[5]王国维对诸宫调研究的贡献还处于概念界定的初步阶段,相关作品只提到《董西厢》《天宝遗事》两部。
冯沅君做《天宝遗事》辑本的时候,辑录了较之更早的诸宫调《刘知远》,“刘知远、董西厢、天宝遗事三部作品,对其研读,引起我进一步探索宋元诸宫调的演变。”[6]她从宫调、曲调、联套、体制等方面发生的转变界定其时间早晚,分别代表了诸宫调发展的不同阶段,然后又从三者对比中总结诸宫调存世三百年的变化。为了证明这一点,她以大量的数字进行举证,为方便起见,列简表如下:
作品 | 《刘知远》 | 董解元《西厢记》 | 《天宝遗事》 | 备注 |
宫调 | 14(13个与宋教坊所用相同) | 15(14个与宋教坊相同) | 10(全部元杂剧散曲所用相同) | 前两部与宋接近,后两部与元接近 |
曲调 | 61(23个见于元曲,占38%。尾声12个,简单。) | 169(55个见于元曲,占33%。尾声13个,简单) | 143(125个见于元曲,占87%。尾声繁复) | 冯先生认为前两部作品的尾声过于简单,统计时应去掉 |
联套 | 一曲一尾最多,没有四曲以上的联套 | 一曲一尾最多,最多有十五曲联套 | 四曲五曲联套最多,长度及曲调配合均与元曲接近 | 前两部联套格式接近,第三部近元曲 |
体制 | 1个引辞,分12章 | 2个引辞,分4卷,不分章 | 3个引辞,原著残缺,分卷分章不得而知 | 引辞由少到多,由简到繁,分章由有到无。 |
冯沅君在深度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出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可举一反三的结论,“时代早者简,时代晚者繁。文辞的华朴且不论,只就数目上着眼便可了然,由一至三”[7]。结论简单质朴,但考证繁琐复杂,反映了冯先生对于学术研究的求实精神。对于厘清戏曲发展脉落、构建戏曲理论体系、深化戏曲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关于“俗讲”的研究
俗讲是唐代流行的寺院讲经形式,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寺塔记上》中有:“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睞,元和末,俗讲僧文淑[8]装之,笔迹尽矣。”[9] 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文叙子》中亦有:“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10]《资治通鉴·唐敬宗宝历二年》中也有“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11]的记载。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对“俗讲”几乎一字未提,其他文献中也都所记不详,因此以往古代戏曲研究对“俗讲”“谈经”多以揣测为主,真实情况难以把握。冯沅君在充分掌握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又以《金瓶梅词话》中的相关描述进行补充论证,找到其中4处讲说佛经的相关内容,进行具体比较分析,归纳出“俗讲”的三个特点:一是讲说时都是有说有唱。二是讲说的题材都是佛教的较通俗的故事,并非什么“空有之义”。三是讲说的目的并非纯粹为宣扬佛法,而是供人娱乐藉以聚敛布施。[12]这就使得人们对俗讲呈现方式的认识更加清晰,其内容和性质也得到进一步明确。在后来各家戏曲史写作中,张庚、郭汉城本《中国戏曲通史》、余从本《中国戏曲史略》、廖奔本《中国戏曲发展史》等关于“俗讲”的内容基本无甚变化。因为可用资料中缺少商人观看“俗讲”的相关记载,张庚、郭汉城本《中国戏曲通史》又引用了唐代白行简《李娃传》长安东街、西街在“凶肆”开展挽歌比赛的内容,作为商人好事的证明,此外还引用元稹《估客乐》、白居易《盐商妇》等唐代诗歌、笔记等作品,同样具有论据功能。
3.关于古代戏曲概念的考证
在戏曲史观方面,冯沅君继承了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基本观点,但同时也做了大量的补充、疏证以及质疑、校正工作,很多古代戏曲概念经过她的考证而更加清晰。冯沅君的《古剧说汇》从“勾栏考”“路岐考”“才人考”“做场考”四个方面进行考证,是其古代戏曲研究的代表之作,表现出深厚的考据之功。
“末尼与乐官”作为宋元优人的名称,是宋元杂剧中的常用概念。末尼现常写为“末泥”。冯沅君在《路岐考》中把它们放到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提出对末尼的理解应改正,而对乐官的理解应补充。她从两条证据出发,认为末尼始终保留着脚色、“当场男子”的原意。一是《青楼集》《蓝采和》中有“后嫁末尼安太平”(小玉梅)、“你是个上戏台的末尼”(蓝采和)等说法,表明末尼即男性主脚演员,也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戏头”。二是宋元戏剧术语常于当时俗语中汲取,而“末”在宋元俗语中可用以指称男子。因此末尼的应用范围不应包含女性演员。她接着对“乐官”的概念进行历史的解释和补充,一连列举了汉、唐、五代、宋、清等各朝各代优人为官现象十几例,充分证明了古人以“乐官”来称呼优人,其实是有其历史的原因。[13]人们的原有认知是依据《蓝采和》《青楼集》而得出的旧推论,冯沅君本着严谨实证的治学态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史料的认识今昔既殊,结论自然不能一仍旧贯。”[14]
经冯沅君考证过的古代戏曲概念很多,单《古剧说汇》就详细考证了“勾栏、构肆、戏台、乐台、乐床、戏房、鬼门道、神楼、腰棚”等出处和内涵。在与前辈或同辈研究学者意见不同时,她大胆质疑,列举证据,发表观点,表现出自觉的问题意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而商榷的过程也是她深入研究论证的过程。
关于“乐床”的概念,冯沅君(在注释中五)提出与余嘉锡商榷:“余嘉锡先生在他的《新续古名家杂剧跋》(见本书晒蓝本,藏北京图书馆)中说:‘剧场谓之勾栏。……内有乐床,为妇女排场之所。’这种解释,我实不敢苟同,虽然在这篇文章内作者有不少的创获。余先生的解释,在第一个例子中,是可以应用的,但用它去解释二、三两例则有点讲不通。‘这里是妇女每做排场的坐处’,‘这是妇女做排场在这里坐’,这两句话不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乐床’是女伶坐的地方?”[15]冯先生有理有据进行辩别,对“乐床”的解释更加明确。这样的考证看似只是细节,但是对于正确理解相去久远的古代戏曲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冯沅君还对余嘉锡上述文章中“乔妆扮”一词的释义进行重新考证。余先生把“乔妆扮”等同于妆扮,他说:“上妆谓之妆扮,亦谓之乔妆扮。”[16]冯先生认为:“‘乔’字的使用在宋元人语言文字中是习见的,它常代表着矫揉造作,装模作样,不真实,不得体的意思。如高文秀的《黑旋风乔教学》(《录鬼薄》卷上,页五),杨显之的《黑旋风乔断案》(同书,同卷,页十三)……蓝采和所以称‘妆扮’为‘乔妆扮’,是因为他已经悟道,不愿再作伶人,为表示轻蔑之意,故在‘妆扮’上加了个‘乔’字,上妆的术语还是‘妆扮’。”[17]梁启超曾评价王国维,“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18],此话显然也适用于冯沅君。冯沅君将“乔”字放在当时语境中进行研究,同时结合《蓝采和》剧情,不仅使“乔妆扮”一词的含义更加精确,而且更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
冯沅君在疏证、质疑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新的材料。比如注释七中提到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他的《中国近世戏剧史》中对金元剧场的讨论,他根据杜善夫《庄家不识勾栏》“抬头觑是钟楼模样”,认为“钟楼”指戏台,当时戏台近乎于今日庙中所见戏台情况。冯沅君不认可这种解释,她认为应将此曲与《蓝采和》“你去那神楼或腰棚上看去”结合起来理解,认为钟楼模样的建筑物就是“神楼”(‘钟楼’言其形状,“神楼”乃其本名)。所以同样以《庄家不识勾栏》为依据,青木正儿将“钟楼”释为戏台,而冯沅君将其释为观众的看席更为合理。
对戏曲从业人员的考证
在冯沅君之前,宋元时惯称编剧本的人为“才人”。但是根据当时“才人”“名公”对称的现象,冯沅君在《才人考》中,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史知识,对其含义重新进行更正。她认为“才人”本与才子同义,即是人之有文才者,因在当时与“名公”对称,所以“才人”用以表示剧作者的身份,而不是剧作者本身。“名公”指达官贵人,“才人”的地位卑下,有低级官吏、遗民、商人、医生、倡优等。“就对于戏剧的贡献论,后者远在前者之上”[19]。
她还进一步考证并丰富了倡优成为才人的例子。“元倡优作家向来多认为只赵文敬、张国宾、红字李二、花李郎四人,实际上杨驹儿是不应该忽略的”[20],并从《录鬼簿》和《青楼集》的相关文献进行论证。另一个倡优才人喜春来,为冯先生从《复道人今乐考证》(著录二,页四)金仁杰《周公旦抱子设朝》下注中的“喜春来按”四字得来,因“喜春来”三字作为曲名解释不通,故以人名释之。但此处未有确切证据,因此冯先生将更深入的考据工作留待日后,“客中无书参证,这个假定的证明势须期之他日。倘若幸而言中,则杨驹儿之外又可增添一个倡优作家”[21]。此亦可算作新史料。
5.关于戏曲服装道具的考证
冯沅君的古代戏曲研究以作品为主,也兼及戏曲服装、道具的考证。戏曲服装有“宁穿破,不穿错”之说,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戏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考证其根源。京剧《击鼓骂曹》中有“为人吃得苦中苦,脱去蓝衫换紫袍”之句。冯先生引《唐书车服志》考证唐代服装的颜色,“一命以黄,再命以黑,三命以纁(浅红),四命以绿,五命以紫。”[22]可见,以紫色为达官服装的颜色,在历史上是有所本的。这就便于观众理解戏曲念白或唱词中常出现的“紫罗兰”一词。比如鲁西北吹腔《挂龙灯》韩英上场诗:“头戴乌纱两翅扇,身穿皇家紫罗兰。腰中紧系八宝玉,粉底朝靴足下穿。”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列举。
冯先生还关注到古代戏曲作品中出现的道具,哪怕是演员手里拿圭这样的细节。她举例说,也是园本《立成汤》楔子的东华仙、文曲星,《钟离春》的齐公子,《渑池会》的秦昭公都用圭,所以“用圭的非诸侯即神仙”[23]。随后她又以《陈抟高卧》作为补充例证,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考证有利于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剧情。
《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更是从十五种钞本“穿关”说明中,“统计得男脚冠类四十六种,衣类四十七种,女脚衣类七种,男脚鞋袜五种,女脚鞋袜一种,女脚头饰八种,男脚巾类六种,鬓发十一种,杂类三十四种。于化妆中,可以窥见有番汉、文武、贵贱、贫富、老少、善恶之别”[24],并最终得出结论,“现行剧场‘行头’多有源于元剧‘穿关’者”[25],证明了古今戏曲舞台在人物服装方面的紧密传承。
6.关于曲调名称的考证
很多曲名不能就字面作简单理解,冯先生以北曲双调【水仙子】为例,如果从字面看,应与水仙花有关,但冯先生引用《武林旧事》“西湖游幸”条所写“歌妓舞鬟严妆自炫以待招呼者,谓之水仙子”为证,认为“水仙子”乃西湖妓女的代称,因此此曲名与妓女有关。她还另举北曲仙吕【油葫芦】为例,此曲与葫芦无关,与蟋蟀有关,冯先生引《帝京景物略》“蟋蟀别种,肥大色泽如油,曰油葫芦”为证,她还另外引用文献,说明斗蟋蟀的历史由来已久。这种考释是有根据的,也是可信的。唯其如此,考证之难,可见一斑。冯先生自己也说:“考释曲调本非易事,我们所敢相信的是大多数曲调名称常代表着一段故事或一种习俗。”[26]
对其他旧说的考证
关于《武林旧事》中“绯绿社”下注“杂剧”的含义,有人认为其为书会之名。冯先生在研究《都城纪胜》《梦粱录》等史料的基础上,认为绯绿社虽以杂剧为主,但它的职务在演不在编。这显然与一般书会的职能是有区别的。
因为《录鬼簿》中提及顾君泽道号九山,所以有人认为九山书会与之有关。经冯先生考证,天一阁本《录鬼簿》中“九山”作“九仙”,显然旧说不能成立。钱南扬先生认为“九山”乃永嘉当地的地名,冯先生认为作地名解释是合理的。[27]
冯沅君古代戏曲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就研究方法来说,冯沅君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考据为主,杂引诸书,相互辩证,并广泛运用文献学、文化学、社会学、训诂学等研究方法,着眼别人所不经意处,从名称入手,探求词源,考释概念,论证周密,观点鲜明,言人所未言。这对于当代戏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也为更深入的历史考证提供了理论观点和材料支持。
1.文献研究法
冯沅君关于古代戏曲理论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中大量使用文献,方法质朴,文风朴实。具体见本文第三部分“文献收集与补充”,此处从略。
2.数据统计法
数据统计即用数量关系揭示事物特征,从而使不确定的、模糊的事物变得相对确定和清晰。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冯先生还在古代戏曲作品中进行了大量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工作,前面关于诸宫调的研究已尽见其详,此处再举一例。宋元时期的一个剧团有多少人员,可能很多学者都未能关注。《元明杂剧·蓝采和》中有“再不将百十口火伴相将领,从今后十二瑶台独自行”[28]的唱词,让人以为当时的戏班可能人数很多。现有资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这是戏曲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冯先生将《元曲选》百种戏剧进行数据统计:每剧4折(惟《赵氏孤儿》5折),加楔子得470个单位,每个单位定为一场,共470场。她又以同样的方法,推算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共84场,每出演出人数具体如下:
《元曲选》共470场 |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共84场 | |||||||
人数 | 2 | 3 | 4 | 5 | 1 | 2 | 3 | 4 |
场数 | 37 | 109 | 136 | 77 | 17 | 15 | 22 | 12 |
359(占总场数的76.4%) | 66(占总场数的78.6%) | |||||||
通过数据统计,冯先生得出结论,当时元剧演出一场7人以上的寥寥可见,主要集中在5人以下,加再上乐队和其他执事人员,一个剧团的人数不会超过30人。如果是人物较少的剧本,十余人也可应付。结论一出,不仅解决了一个长期无人回答的问题,也证明了《蓝采和》“百十口火伴”的说法是夸张的,不符合元代戏班的事实。[29]
3.以诗证史
以诗证史,这里的“诗”泛指各种文学作品,它是指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依据相同社会背景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推理方法,到文学作品中寻求帮助。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运用此研究方法,依据《水浒传》与周宪王的杂剧来探讨金元的院本。冯沅君非常赞同这种做法,她说:“这种搜集文学史的方法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因为天才的作者,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作者,在致力创作的时候,常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种种动态巧妙而忠实的织在他们的云锦里。所以历史的研究者,无论其为文学史的研究者,抑经济史的研究者,社会史的研究者,……都应该将自己的矿山拓大,不应该忽视几种著名的长篇小说中的史料。在几种著名的明代长篇小说中,金瓶梅词话所供给的文学史料实比其他各书为多。”
冯沅君吸收并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以《金瓶梅》中的相关内容作为古代戏曲研究的论证材料,不仅表现出冯沅君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新的方法,更表现出其超人的胆识和超前的学术判断能力,毕竟《金瓶梅》曾长期被视为淫书。她对《金瓶梅》中与古代戏曲相关的信息进行梳理,从“俗讲的推测、小说蜕变的遗迹、曲的盛行、笑乐院本的一个实例、演剧描写的启示、清唱的曲辞与唱法”等六个方面展开研究,对古代戏曲发展进程记载缺略的各个环节做进一步考证。民国时期,《金瓶梅》刚刚从禁书被允许阅读,而她却从其中寻求文学史料,而且取得了另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可谓开学术风气之先。
在冯先生的古代戏曲研究中,还多次引用《水浒传》作为研究史料。关于古剧中的“砌末”,冯沅君在《古剧说汇》中认为“演剧时将‘砌末’挂起来,表示某伶在做场”[30],因为《元明杂剧·蓝采和》中有“王把色,你将旗、牌、账额、神帧[31](左巾右争)、靠背,都与我挂了者”[32]。在文后注释中,她又引用《水浒传》小说的相关描述作为进一步的证明:“雷横听了,又遇心闲,便和那李小二到那勾阑里来看。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33]据此,冯沅君得出结论,“若果《水浒》所叙确有所本,则蓝采和所教王把色悬的也是在勾阑门口,惟其是在门口,所以见者便知他是‘做场’。”[34]
为了使宋元杂剧“村里赶赛处”的演出情形更加形象生动,她还引用了《水浒传》一百三、四两回“乡村做场”的场面为证。其中关于演出现场情形的描写如下:
庄客道:“李大官人不知,这里西去一里有余,乃是定山堡内段家庄。向本州接得个粉头,搭戏台,说唱诸般宫调。那粉头是西京来新踅的行院,色艺双绝,赚得人山人海价看,大官人何不到那里睃一睃。”话说当下王庆闯到定山堡,那里有五六百人家。那戏台却在堡东麦地上。那时粉头还未上台,台下四面有三四十只桌子,都有人围挤着在那里掷骰赌钱。[35]
这段描写不仅交待了农村戏台坐落的位置、四面观的看戏方式,还交待了噪杂的演出环境,戏曲研究以小说描写为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戏曲史料的不足。虽然小说成书年代较晚,但考虑到戏曲演出的因袭性,“当时优人的生活或者从此尚可得其仿佛”[36],因此,以所得明清史料补宋元文献之不足,冯沅君谓之为“沿波讨源”。
以诗证史,这是冯沅君利用文学史料“将自己的矿山拓大”的研究方法,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通性之真实”,即以合乎逻辑的想象对历史的真实加以阐明、推断乃至于大胆填补。这也成为后来广大戏曲研究者学习和效仿的常用方法,如孙崇涛《戏剧史料辑考》(《文化遗产》2015(6))、顾春芳《戏曲剧目及各类演出考证补遗》(《曹雪芹研究》2018(1))等,均为依据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古代戏曲史料,考察不同阶段的戏曲形态及其渊源,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
4.旁证、互证、反证
因考释内容复杂多样,冯沅君的研究方法往往不拘一格,有旁证,有互证,也有反证,可谓灵活多变。《路歧考》中提到宋元女性优人一般还兼酒楼茶肆中应召献技,冯沅君首先以《太平乐府》中无名氏的“拘刷行院”【耍孩儿】散套为据,又引《宦门子弟错立身》作为旁证,同时指出,剧中完颜寿马在茶肆中见到写有“王金榜”名字的招子,应是根据当时茶肆酒楼做场的习俗而设计的情节。语言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从“磕脑”一词的用法推测《张协状元》产生的年代,同样可作为旁证之例。作为现存最早的戏曲剧本,《张协状元》产生的年代对于戏曲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经冯先生考证,认为“磕脑”系指头巾,宋元时期的惯用语。根据《张协状元》的体制、排场以及“磕脑”一词的用法,冯先生认为它与其他南戏不同,它的年代要早得多,“如非宋作,则应在元朝早年”[37]。为了进一步证实此判断的可信性,她又以《三国志平话》《水浒》中均使用“磕脑”一词为据,作为推测《张协状元》产生年代的旁证。
《路歧考》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关于宋元优人何以常有亲属关系以及剧场上是否男女合演的问题。王国维《古剧脚色考》余说四“男女合演考”中曾提到:“盖宋元以后,男可装旦,女可为末,自不容有合演之事。”[38]冯沅君认为,古人的社会地位或者职业大都是世袭的,所以会有生而为奴则世世为奴的现象。优人亦是如此。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并不适用当时舞台上的倡优之间。冯沅君从社会发展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在男女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社会里,倡优尽可男女混杂,何况他们彼此间又常有亲属关系。因男女须有别而令男女分演,这也许竟可视为优人身分的提高……它应是男女合演以后的现象。至于现在的男女合演,那是男女关系解放的结果,与古代的男女合演似同而实异。”[39]冯沅君据此判断王国维所说宋元以降“不容有合演之事”是武断的。她随后以《蓝采和》为例,蓝采和的家庭戏班以蓝采和的妻子喜千金和儿媳蓝山景为主要演员,男演员包括蓝采和、小采和、王把色、李薄头,这样的组班方式确定是男女合演的。因此,此段史料从正面证实了冯沅君古代男女合演的观点,同时也成为“不容有合演之事”一说的反证。
宋元杂剧中的“脱膊杂剧”常与古人作战或打擂有关。冯沅君在《才人考》中采用了两段史料互证的方法对“脱膊”一词进行探源。一是《也是园古今杂剧钞本》中《刘千病打独角牛》一剧,内有“独角牛做脱膊科”;二是《水浒》七十四回《燕青智打擎天柱》中有“你且脱膊下来看”。冯先生由此判断“脱膊”即脱去衣服,乃当时常用词,或为当时俗语。两段史料,一段杂剧,一段小说,虽体裁不同,却参互辩证,使“脱膊”一词的概念更加清晰,也更有助于人们对“脱膊杂剧”的理解。[40]冯先生还把美术作品拿来与她的戏曲假面研究互证。她在《做场考》中提到,“也是园本各剧穿关未戴假面,其他元剧中也未透露使用假面的消息。不过宋人演剧确曾用到它,宋苏汉臣《五瑞图》可证。”[41] 该画作藏于故宫博物院,据李家瑞先生考定,他画的是“五花爨弄”,在右下方的一个“绿衣持简,戴花脸面,作逃避姿势,此即五花爨弄中之副净也。”(摘自云南大学学报,第一类第一号,《苏汉臣五花爨弄图说》)[42]这幅美术作品成为冯先生假面研究的依据。
5.训诂研究法
因为面临着古代戏曲资料不足的难题,冯先生很多成果又是完成于抗战时期,给学术研究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她在没有文献资料可依据的情况下,灵活运用“因声求义,综合比较”的训诂研究,在概念考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路歧考》关于“则剧”一词的考证。《齐东野语》《张协状元》《武林旧事》中都出现过“则剧”一词,而“则”字如何理解学界尚无明确解释,有人简单地把它当作是作者讹误。冯先生不以为然,她广泛列举此词出处,用训诂学的方法加以解释:“则剧既屡见于宋元人书中,可见它在当时颇流行,决不能视为偶然的错误。意既难解,姑就字音上推究。我们猜想则剧殆是杂剧。‘杂’‘则’音近,以‘则剧’为‘杂剧’。当如‘砌末’、‘丝末’之为‘细末’,‘傅末’、‘付末’之为‘副末’。当初本是同音或音近通假,后来竟二者并存,甚且喧宾夺主。”[43]
《辍耕录》中认为“爨”乃“五花爨弄”之省,与爨国有关。冯先生认为,就与此有关的文献看,它与艳段殆为同实异名。钱南扬认为爨乃艳字的促音,冯先生从训诂学角度却不同意此类说法,她认为爨乃艳字的通假。她认为“爨”与“段”虽是叠韵,但“爨”与“艳”并非双声,所以不会产生这种促读。考“爨”属翰韵(兼属寒韵),艳,焰属艳韵,同为去声,前者收N,后者收M,依常例,同收N者可通叶,所谓半韵者是,同收M亦然。因为二字的韵(收声)相近之故,“爨”与“艳”相通。[44]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将“诨砌”的“砌”解释为“滑稽玩笑”,冯沅君采纳了这一观点,但是在文字考证方面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她将“砌”字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研究,认为“砌”是宋元人的常用字,“打诨”与“打砌”意义相同或接近,“诨砌”连用与“诙谐”连用同。她还另外从不同角度提供考证材料,广征博引,从《谷粱传》《张协状元》《元曲选》中“砌”字的相近用法,证明“诨砌”一词的“砌”字,实与“诨”同义。[45]因此,冯沅君对《宋元戏曲考》的补充,还表现在她对某些词语的深刻考订。
6.中西戏剧比较
冯沅君在民国时期已自觉使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问题。
关于宋元古剧场的考证,冯先生引用《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英国古剧场的描写:“在中古期,有神道场面的宗教剧是戏剧中最为人喜爱的一种。并没有专为它建筑的场所,演出大都在教堂或临时搭的棚子中。当十六世纪,非宗教的戏剧场复兴。这在伊利沙白朝是英国文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其演出是在帐棚、木房或旅馆的庭院中。直到该世纪末,在莎士比亚与布贝基的管理下方有固定场所准许演剧。”[46]通过比较,冯先生发现了“中西剧场发展的共同途径”,那就是它们都经历了由不固定到固定的过程,观众根据财富、身份分层,所以看席有高低上下之分。
为了说明中外伶人在历史都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冯先生还引用莫里哀的例子作为证据[47]。相传莫里哀决定献身戏剧时,他的父母非常不喜欢,认为这种职业伤风败俗,为宗教所排斥(《莫里哀全集》王了一译,商务版,第10页)。他的家人也曾请一位教士劝他,说这样会丧失了家庭名誉。这和中国古代戏曲演员的处境是一样的,虽然人们需要看戏,但是却瞧不起从事这个职业的艺人。
冯先生在《古优解》[48]中还将欧洲中世纪的fou与中国先秦西汉之俳优进行对比,因为fou同样是以诙谐乐舞受人主贵族所豢养,其身份与优相类似,这样就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研究视野更为开阔。
三、冯沅君古代戏曲研究的文献学价值
冯先生的治学特点是围绕着要考证的问题提出观点,然后广泛收集有关文献作为佐证,充分表现出治学重考证,“考据为本”、“无征不信”的特点。也因此冯先生的古代戏曲研究成果中列举的大量相关书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她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对已有研究成果提出质疑,并进行论证,有的得出可信的结论,有的暂时存疑,留待日后深入研究,这些成果本身又成为当代戏曲研究参考和借鉴的重要文献。
1.文献引证与补充
以冯先生《古剧四考》中的“勾栏考”为例,如果不含引证材料,作者本人的论述仅寥寥数语,提炼如下:“宋元时的剧场叫做‘勾栏’。(此处略去《梦华录》《武林旧事》《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宦门子弟错立身》《元明杂剧》《青楼集》相关文献引用13处。)有时叫做‘构肆’。(此处略去《梦华录》《元曲选》相关文献引用2处。)勾栏似乎有棚为之。(此处略去《梦华录》《元明杂剧》相关文献引用3处。)勾栏内有‘戏台’,是演戏的地方。(此处略去《元明杂剧》相关文献引用3处。)戏台有时叫做‘乐台’。(此处略去《元明杂剧》相关文献引用1处。)勾栏内又有‘乐床’,是女伶所坐的地方。(此处略去《元明杂剧》相关文献引用4处。)又有‘戏房’即后台。(此处略去《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宦门子弟错立身》相关文献引用3处。)又有‘鬼门道’,或称‘古门’,乃‘戏房出入之所’。(此处略去《元曲选》相关文献引用3处。)又有‘神楼’和‘腰棚’,这是看席。(此处略去《太平乐府》《元明杂剧》相关文献引用5处。)勾栏的规模往往很大。(此处略去《梦华录》《辍耕录》相关文献引用3处。)这是就固定的剧场言。据故书所载,还有些伶人不在一定的‘勾栏’内演剧。任何宽敞热闹的地方都可做他们的剧场。(此处略去《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相关文献引用2处。)那么一切的布置当然都要从简了。”[49]
短短一段话,每一单句后面均紧接2至13处数量不一、长短不等的文献佐证材料,共计42处,涉及古文献8种,通过佐证材料对勾栏的设置、功用、规模等进行实证说明。更难能可贵的是,冯先生严格遵循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为了复查方便,所有引文均详细标注书目、版本、页码以及某些孤本的藏书之处,这样的学术研究规范在民国之时显然走在了前列。
该文正文以“考据为本”,从字面上看,丰富而翔实的文献资料包裹着作者对于勾栏简洁朴实的总结和概括,几乎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其考证之功让人感觉字字千钧。但比较来看,就会发现作者更为深厚的研究功力、更为严谨的治学态度还隐藏在正文后面的注释中。以“勾栏”这一概念的考证为例,正文中作者首先定义勾栏为“宋元时的剧场”,后面即包含“勾栏”一词在各种古文献中的出处。而文后的注释,作者又做了进一步补充说明:
“勾栏”,或作“构阑”,“构栏”,“勾栏”。它本是殿堂上的阑干,所以李诫在营造法式上以“勾阑”来注释鲁灵光殿赋的“轩槛”与景幅殿赋的“棂栏”(营造法式,一九二五年刊本,卷二,页七至八),并且绘有图样(卷二十九,页十一,卷三十二,页十六)。《梦华录》“般载杂卖”条(卷三,页四)的“箱如构栏”,“皇后出乘舆”条(卷四,页二)的“前后有小勾栏”,则又将殿堂上的阑干的名称用于车上。至于用这两个字称剧场和其他演奏技艺的场所的原因,大约是因为“艺人”在表演时用阑干将他们自己与观众分开之故。[50]
可见,就连文后注释也同样以文献引证观点。正文中没有涉及“阑干”一词的本义,以及以“勾栏”代指宋元剧场的原因,注释中一并做了补充。这也是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未曾提及的。
冯沅君古代戏曲研究成果中,不仅收集了大量相关文献,还在论证过程中列举了大量古代戏曲剧目及演员,同样具有文献价值。例如《路歧考》中“老优作教师,操乐器”部分,提到无名氏《梦笔叙》记钱岱家有女教师沈娘娘教戏,附记演习院本有《跃鲤记》《琵琶记》《钗钏记》《西厢记》《双珠记》《牡丹亭》《红梨记》《浣纱记》《荆钗记》《玉簪记》等十本[51],这段转录一方面说明这些经典剧目早在宋元时期已在民间流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冯沅君继续推论其时间,因为钱岱是隆庆辛未(1571年)进士,大致可知其时间应在明中期,而上列剧目又曾出现于元杂剧中,“明承元风于此可见”[52]。而从沈娘娘教习之事,又论及清代优人于得名后往往招收门徒的历史现象,“成立某某堂以训练后起的演员,如梅巧玲的景龢堂,刘倩云的春龢堂,孙心兰的乐安堂等。这种风气也可以说是其来有自。”[53]而在注释中又详细补充了以上信息:
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青衣梅巧玲生”条:“……出师后自营景龢堂于李铁拐斜街,后掌四喜部,授徒甚众,如余紫云(花旦兼青衣),张瑞云(武生),孙福云(武旦),陈啸云(青衣兼小生),姚祥云(昆老生),外号半截,即姚佩秋、姚佩兰之父,刘朵云(花旦),郑桐云(武老生),董度云(小生),陈五云(花旦),高倩云(昆旦),刘曼云、朱蔼云(昆旦,字霞苏,即朱幼芬之父),王湘云(昆小生),王桐云(花旦),周绮云(昆旦),郑燕云(昆旦兼花旦)。[54]
此引文罗列了梅巧玲的一众弟子,同时将他们家庭成员中的其他知名演员也作了列举,师承关系、父子关系得以梳理,冯沅君在此引用此文,既可为正文中提到的观点作证,又可为后学者研究京剧发展历史提供依据。
冯沅君在戏曲研究过程中时有发现他人未曾发现的新史料,例如《才人考》中提到的“掌记”。冯沅君在《太平乐府》《武林旧事》中都找到了关于“掌记”的简短资料,这是她的新发现。她把新资料与《宦门子弟错立身》合看,得出对“掌记”一词更加丰富的认识:它指的是优人随身携带的剧本,因其体小袖珍,而以“掌”字形容其大小。“掌记”还是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优人要演新戏,就会争相购买市场上传抄的新剧本。[55]
另外,冯沅君的《南戏拾遗》以大量精力考释传奇本事,《南戏拾遗补》补充考释十六种本事,不仅具有辑佚作用,还以元杂剧为南戏考证补遗,为南戏更深入地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和方法。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以及更加长远的将来,当古代文献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稀有和难以查找,冯先生当年对古文献的引证和补充工作就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学术质疑与修正
学术研究需要争鸣。冯沅君关于古代戏曲研究的商榷文章,多次提到吴晓铃先生。吴先生也曾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写过《冯沅君“才人考”辨正》[56]做为回应,当时正值日军侵华,北京沦陷,幸好文章得以保存。吴先生随当年的北京大学南迁,定稿即完成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的云南。试想战乱流离的年代,两位前辈学者依然能够心无旁鹜,专心治学,审慎考证,各抒己见,这种治学精神实令今人感佩。
在研究关汉卿出生问题上,吴晓铃有“大德歌可能作于大德初”的推断,冯沅君对此提出质疑,并进一步对“大德”一词进行考证。她认为把“大德歌”中的“大德”理解为年号,这只是字面上的解释,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与年号相同的曲调未必就一定是从年号来的。她举出两个反证——“嘉庆子”和“元和令”。“嘉庆子”是一种卖水果的叫声,源于当时“凡卖一物必有声韵,而吟叫不同”[57]的习惯;“元和令”出自于郑元和的故事,唐宋以来盛行于民间,为瓦舍艺人所熟知。可见,无论是“嘉庆子”还是“元和令”,都与“嘉庆”“元和”的年号无关。虽然后来的戏曲史撰写大多延续把“大德”理解为年号,但冯先生的观点亦有理有据,值得进一步求证。
关于关汉卿的生卒年,吴晓铃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应生于1224年左右,卒于1300年左右。冯先生把与钟嗣成有过交往的杨维桢、朱经的生活年代作为参照,同时又以钟嗣成生活年代与好友朱经作参照,经过论证后对吴晓铃的结论提出质疑。同时她还结合关汉卿年代、籍贯的各种不同说法,提出自己新的设想:关汉卿可能不止一个,存在重名的可能。即使结论相同,冯先生也会提出自己不同的依据。“我们虽然也将剧家关汉卿拉到元代,但所持的理由却与前二说不尽同。他们重视大德歌,以此出于元成宗年号,我们不然,于【一枝花】套外,还有两项依据”[58],一是文人成就归于时代,1300年前后数十年,元剧极盛,马致远应属于此时代;二是以马致远为参照,因为他与关汉卿在《录鬼簿》中都被列入“前辈名公才人”,因此从马致远资料可以大略推知关汉卿生年应在1240年左右。这种推测有一定的依据,却又不敢确定,因此冯先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继续研究的希望寄予后人。她说:“当史料缺乏的今日,这还是两个不敢贸贸然解答的问题,只好期之于将来。”[59]余从本戏曲史采取模糊说,“约生于金朝末年或元太宗时”[60],廖奔本戏曲史则认为应为1214年前后[61]。之后又有多位学者对此问题展开研究,如尚达翔《关汉卿生卒年新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胡世厚《关汉卿卒年新考》(《东南大学学报》2019(3))等,都试图提出新的依据和观点,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这样的代序传承却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厚实的根基。
结论
以《古剧说汇》为代表的冯沅君古代戏曲研究成果,完成于1935-1945年间,正是中国内忧外乱之时,南北颠连,居无定所,手边可用文献不足,这也限制了她的研究。冯先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局限,她在《才人考》“院本名称”中曾提到:“现在提出来讨论的也只以么麽院本,么末院本,拴搐艳段,与冲撞引首四者为主,旁及于院爨,院么,余则期之他日。”[62]包括前面提到因为资料缺乏“不敢贸贸然回答的问题”,以及提出质疑尚未得到共识的问题,都应该属于冯先生“期之他日”的问题,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期之他日”的问题依旧还是问题。虽然冯先生的古代戏曲研究成果至今仍被承认和使用,其研究方法也在后学者身上得到了进一步传承和光大,其辑佚和考证的古代戏曲文献也更愈显其珍贵,但是先生学术考证中存在的争议以及“期之他日”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地推进,其研究成果中的新发现也未引起后学者足够的重视,与先生其他成果的关注度、传播度相比,其古代戏曲研究成果在学界受到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很多有益的成分未曾被吸纳。
当前古代戏曲理论研究成果众多,取得突破者有之,重复研究、自说自话者亦有之,重提冯沅君,不是为其个人学术生涯做总结,而是要呼唤她那种接续传统、勇于探讨的精神。当然,理论观点见仁见智,加之所处时代的局限,冯先生的研究成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前期主要表现为战乱年代资料不足,后期主要表现为“文革”时期受到阶级观影响),在各种考证和质疑的观点中,也还存在着某些偏颇和疏漏,有待后学者进一步客观地辨识、深入地研究。冯先生一生治学,其丰厚的研究成果、严谨的治学方法、执著的探索精神、非凡的学术勇气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冯先生古代戏曲理论研究的当代价值,也应该成为所有理论工作者最为宝贵的精神气质。
(原文发表于《戏曲艺术》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周爱华(1971-),女,博士,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评协副主席。研究方向:戏曲美学与地方戏曲。
1.李玫:《古代戏曲研究风尚得失谈》,《文学遗产》2016(6)。
2.转引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3.转引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6.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页。
7.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71页。
8.经前人考证,文淑与文溆、文叙乃同一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俗讲僧。
9.(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2页。
10.(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11.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50页。
12.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页。
13.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9页。
14.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9页。
15.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3页。
16.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17.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18.梁启超:《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19.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20.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98页。
21.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99页。
22.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15页。
23.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页。
24.《国书介绍: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冯沅君著),《国书季刊》1944年新5第4期,第103页。
25.《国书介绍: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冯沅君著),《国书季刊》1944年新5第4期,第103页。
26.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03页。
27.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99页。
28.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
29.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3-54页。
30.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6页。
31.未找到此字的对应字,以帧代之。原文中写作左巾右争。
32.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6页。
33.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
34.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
35.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36.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37.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13页。
38.王国维:《王国维论剧》,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39.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2页。
40.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62页。
41.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42.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17-118页。
43.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92页。
44.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11页。
45.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46.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7页。
47.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93页。
48.冯沅君:《古优解》,重庆商务印书馆三十三年一月出版。
49.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
50.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2-33页。
51.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52.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53.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54.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98页。
55.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
56.吴晓铃:《冯沅君“才人考”辨正》,《读书通讯》1942年第54期。
57.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64页。
58.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69页
56.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60.余从、周育德、金水:《中国戏曲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61.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二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62.冯沅君:《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责编:
审核:陈凤祁
责编:陈凤祁

金价接连跳水,相关话题冲上热搜第一
中新网微信公众号

未来月球上能打电话盖房子?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回应
人民日报客户端

巴菲特支持特朗普关税计划?回应来了:假的
央视新闻

“断层式”领先!陈芋汐、全红婵包揽跳水世界杯女子10米台冠亚军
央视体育

坚决反对!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就美征收所谓“对等关税”一事发表声明
央视新闻客户端

美加税加到内伤 特朗普又催降息 纳指“自由落体”进熊市
央视新闻客户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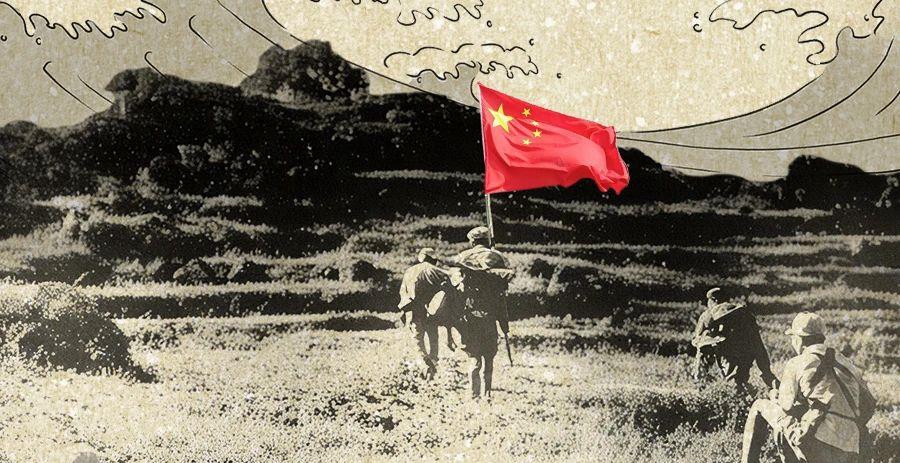
历史早已写下答案!为了这个省 他们用生命铺路
央视军事
网传深圳北站地铁站扶梯发生踩踏事故,工作人员回应
大河报

江苏、上海等地惊现“火球”,不少人拍到了!专家发声
东方网

清明假期山东文旅市场亮点纷呈:山岳游受热捧 短途周边游成主流
大众报业·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