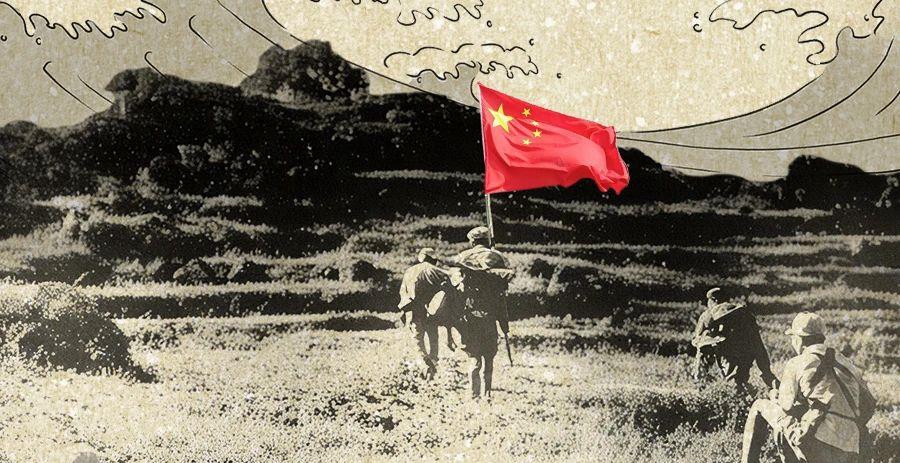大众网
李 伟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要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历史,找到千百年来延绵不绝的优秀“文化基因”所在,首先离不开对孔、孟的研究。如果说孔子是五千年“中华文化之中点”(《中国文化史》),那么孟子就是“继往圣,开来学”的关键一环。而关注孟子在中国文化学术传承中的定位,首先应关注孟子与汉代经学之关联;而作为汉代经学“喉衿”的诗学,又是应当着重关注之处。然而在汉代《诗》学的传授谱系中,孟子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却因时间久远、典籍难征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二十世纪后期,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的发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学界关于周秦两汉时期的一些定见也得以深化或改观,孟子与汉代《诗》学之间的深层关系也得以端倪初现。
近期,李华教授《孟子与汉代四家诗》一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致力于厘清孟子与汉代《诗》学之间的深层关系。这是李华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潜心增益十余年的结果。我们在此转发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关于汉代四家诗的《诗》学渊源,人们多习惯将之溯源至荀子,甚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宋人之学为直接孟氏,汉人之学为源于荀卿”的观点。然而深入探讨汉代《诗》学的发展历程和内在特质可以发现,孟子才是汉代四家诗取法仿效的主要对象。由此,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也应予以重新估量。
一、传统“祖荀”观——读《诗》“不知荀义,是数典而忘祖也”
荀子素来被学界视为汉代四家诗的直接导源,甚至被视作汉代五经之学的直接源头,这一观点始于两汉、盛于清代、并相沿至今。
典籍中最早言及荀子与四家诗关系的是《汉书·楚元王传》,其中提到鲁诗学者申培公是荀子的再传弟子:“(楚元王)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虽然这一论述并没有明言申公对荀子《诗》学的承袭,然而此论却开后世《诗》学“祖荀”说先河,后世学者论及鲁诗乃至四家诗渊源时,无不据此溯源至荀子。如南宋范处义的《诗补传》便据此称:“《鲁诗》出于浮丘伯,乃荀卿门人,……则荀卿……乃《鲁诗》之源流也。”
汉宋之间诗学的“祖荀”观主要集中于鲁诗、毛诗渊源上,而并未涉及荀子与四家诗之间的整体关联;而到清代,“宋人之学为直接孟氏,汉人之学为源于荀卿”的观点极为盛行,清儒对荀子在汉代诗学传承中的地位的关注与彰显发展至极致。例如,皮锡瑞《经学历史》就曾指出汉代五经之学均与荀子密切相关,而四家诗更与荀子存在直接渊源:“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严可均也曾作《荀子当从祀议》表彰荀子传经之功:“荀子非但传《礼》传《乐》也,又传《诗》传《春秋》。”
“汉人之学为源于荀卿”的观点不仅在清代广为盛行,也得到了近现代学者的普遍认可。例如刘师培先生在《经学教科书》中称荀子为“《鲁诗》之祖”“《毛诗》之祖”;刘汝霖先生《汉晋学术编年·鲁诗传授表》首列荀卿;范文澜先生在《群经概论》第四章《诗》中亦持论相同。马积高先生《荀学源流》甚至明确指出了荀子在汉代四家诗发展过程中的功劳之巨甚至已足以越过子夏,而直接担当从孔子《诗》学到汉代四家诗之间的发展承传环节。
荀子为汉代四家诗渊源一说,沿袭者久、承传者众,甚至前人曾有读《诗》而不知《荀子》,“是数典而忘祖”之叹。相对而言,孟子则多被简单视作孔荀之学的连结者、以及汉代《诗》的经学化进程的中间环节。汉代《诗》学对荀子虽不乏承传,但影响汉代《诗》学发展至深的诸多关键因素却均与孟子密切相关。
二、汉代《诗》学中“宗孟”现象——“虽云枝叶扶疏,实亦波澜莫二”
透过笼罩于荀子身上的层层光环,深入探讨孟子与汉代《诗》学的关联能够发现:在关乎汉代《诗》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上,包括经学化历程、阐释路径的选择等诸多方面,汉代《诗》学发展体现出了鲜明的宗孟倾向。
(一)从“诗”到“经”:汉《诗》的经学化基调赖孟子而定从汉代《诗》学发展的经学化道路来看,诸多学者均倾向于把荀子视作先秦儒家《诗》的经学化发展的最后环节、以及汉代《诗》的经学价值确立的最初阶段。诚然,荀子的礼学思想及其对《诗》的大规模引用,对于《诗》的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贡献匪浅。但深入探究汉代《诗》学发展的经学化历程却能够清楚看到,汉代《诗》的经学化发展历程主要是沿着孟子所规定的《诗》学道路进行的。
五经之中,唯独《诗》的体式最为特别,其他四经均以文本形式出现,而《诗》的教化意义的彰显却一度要依赖于乐、舞的共同配合。而随着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现象的加剧,乐、舞逐渐缺失,如何把原来由三者共同承载的教化意义集于《诗》之一体,这对继承孔门《诗》学、把《诗》奉为圭臬的儒家学者而言是一个重大课题。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内部的不同学派均有不同尝试,根据其倾向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派别:其中一部分学者仍然坚持旧有的诗乐结合的传统,重视对《诗》的教化功能的阐发,相关著作和学者以《孔子诗论》、公孙尼子和荀子为代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避谈乐教,而选择从《诗》的文本出发寻找其中所蕴含的教化意义,这主要以思孟学派的子思和孟子最为代表。子思一派的学者更加注重对《诗》的道德内涵的解读,孟子则最早赋予了《诗》之文本以王道政教意义。
孟子对《诗》之文本的政教意义赋予,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完成的:
首先,孟子通过“迹熄诗亡”“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诗》学观确立了《诗》的文本阐释方式:“迹熄诗亡”观把《诗》的创作纳入到王道盛衰的历史序列中,视《诗》为王道制度的承载者和反映者,从而对《诗》的解读和对王道盛衰的关注便被紧密关联在一起;“知人论世”观指出了《诗》是对作者创作背景和创作意旨的如实反映,从而对王道盛衰和作者创作意图的关注便被纳入到《诗》的文本阐释范畴之中;此外,“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又确立了说《诗》者的主体性地位,从此《诗》不再仅仅是创作者意旨的表达,也成为传达阐释者意图的重要途径和工具,这同时也意味着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现实的需要而赋予《诗》以王道政教主旨。从西方文学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孟子对《诗》之文本的王道政教价值的界定,涵盖了《诗》之文本从产生背景、作者意图、文本价值和读者立场等所有的传播层面和传播环节。由于以上每一个环节均与王道政教密切相关,这为后世解读者从任何一个环节发现和阐释《诗》的政教价值提供了可能性。其二,在具体的《诗》学实践过程中,孟子又高度关注《诗》的字句释义,这种直接诉诸文本的阐释方式使得《诗》得以摆脱了乐、舞的辅助与限制,凭借文本释义而拥有了独立的政教意义,乐、舞仪式中所蕴含着的政教意义和庄严特点,也由此得以借助文本之《诗》流传于世。
孟子对《诗》的文本价值的重视与政教意义的彰显曾引起了荀子的极大不满,他的一些代表性的《诗》学观点正与孟子针锋相对:“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是俗儒者也。”荀子不仅反对《诗》的承传授受、把传授《诗》《书》的儒生归入“陋儒”之列,而且明确提出了“隆礼义”“杀《诗》《书》”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汉儒在承袭前人之说时,却绕开了在时间上相距较近且学说流传在汉代较为广泛的荀子,而直接上承孟子。由孟子所创建的注重文本政教意义阐发的《诗》学诠释方式不仅被汉代四家诗学者全然接受,并且在汉代《诗》经学化进程中也多有展现:
其一,四家诗对《诗》的文本价值的重视。
据记载,《诗》流传至汉代可以和乐而歌者几乎百不存一,然而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诗》在汉代的蓬勃发展。究其原因,这与汉代《诗》学承袭孟子余续、高度重视《诗》的文本价值密切相关。
汉代四家诗对《诗》之文本释义的关注,为《诗》的经学价值的获得准备了必要条件。《易》《诗》《书》《礼》《春秋》,多以文本形式传世,唯有《诗》经历了一个与乐舞结合的过程,甚至一度离开了乐舞的支撑便难以传达完整的教化功能。然而关注《诗》之文本的阐释方式的确立,却把乐舞承载的政教性特征完全转移至《诗》之一身,从而《诗》得以以文本的方式展开释义,能够凭借文本承载全部的教化意义。
查考汉代四家诗的《诗》义阐释能够发现,汉代四家诗对《诗》的关注呈现出鲜明的注重训诂的特色,其中尤以鲁诗和毛诗最为代表。四家诗中最早出现的鲁诗,便非常关注《诗》的字义训诂,这种对《诗》之文本的重视正与孟子解《诗》一脉相承;毛诗的《诗》学阐释表现与鲁诗极为相似,其代表著作之一《毛诗故训传》便是从对《诗》的字、词、句、篇的释义层层着手的,甚至其阐释内容与方式亦与孟子多有相合;韩诗虽不着重对《诗》中字词的训诂,但其释义也是从《诗》的基本单位即《诗》句入手的。
其二,四家诗对《诗》的政教功能的彰显。
孟子对《诗》的定位和运用,充满了王道政教性的价值指向;而汉儒解《诗》用《诗》的王道政教意图也与孟子多有关联。首先,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王道《诗》学定位,均被四家诗纳入其核心《诗》学价值体系之中。从鲁诗到郑玄,均不约而同地把《诗》对王道政教的承载作为《诗》义解读的第一要义。鲁诗的“四始”说是鲁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的纲领性观点,《诗》的经学化意义正是由此得以初步确定的。然而通观鲁诗的“四始”设置却会发现,鲁诗“四诗”恰好对应了周代王道发展从初兴、兴盛到中衰、没落的四个过程,这正是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的切实反映。作为鲁诗乃至汉代四家诗中纲领性观点,鲁诗“四始”说对孟子的承袭,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孟子的“迹熄诗亡”说在汉代《诗》的经学化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此外,齐诗的“四始”、“五际”说同样是以《诗》对应王道盛衰的具体过程,虽然表现形式有异,但在对孟子的承袭上却与鲁诗殊途同归;韩诗《关雎》“为王道之原”的观点,《毛诗序》中《风》《雅》《颂》各序的排列顺序,《毛诗故训传》的诗义阐释意图,郑玄《毛诗谱》的整体旨归也无不与孟子的“迹熄诗亡”说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汉代《诗》学对王道政教阐释倾向的重视,与孟子对《诗》的王道政教意义的价值定位密切相关。
汉代四家诗在《诗》的政教阐释方面对孟子的承袭难以一一尽指,但以上所列已经足以表明,汉代四家诗对《诗》的文本释义的高度重视、对《诗》的经世致用价值的附会与阐发,无不是遵从孟子的《诗》学理路而来的。
(二)“政教”与“性情”: 汉《诗》双重阐释路径由孟子而开汉代《诗》学发展,重政教亦重性情,关于其政教化释义渊源,学界普遍将其归结至孟子;然而汉代《诗》学重性情的渊源何在,却素来是学界争讼之端。
汉代《诗》学的重情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者是对《诗》中性情意义的阐发,这一特点导源于《孔子诗论》已成定见;另一种是对《诗》的“情”本思想定位,这主要表现为齐诗的《诗》“原性情”说和毛诗的《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这种“情”本思想不仅是汉代《诗》的性情化阐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后世“诗缘情”观点的萌蘖之端。关于“发乎情”说思想渊源,目前学界的主要指向包括:荀子的以礼节情观、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以及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性自命出》。
深入探讨以上三种观点可以发现:《毛诗序》中的《诗》“止乎礼义”一说,其与荀子“以礼节情”的思想确实渊源可判,然而“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核心即“情”本思想,却与荀子没有直接关联;而《孔子诗论》中虽不乏以“情”解《诗》的部分,然而它对“情”的定位却与“发乎情”的观点截然相反:《孔子诗论》认为“情”是通过《诗》传达和表现出来的,是《诗》的阐释终点;而毛诗却认为《诗》“发乎情”,“情”是《诗》的根本导源,也是《诗》的创作起点。虽然两种观点均肯定了《诗》与“情”的关联,然而两者的立足点却截然不同,不可等而视之。故而也不应把“发乎情”的观点简单归因于《孔子诗论》;三者之中,唯有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曾经明确提出过“道生于情”的“情”本观点,这种对“情”的导源意义的强调,已经初开毛诗“发乎情”的思想之端。不过人们却忽视了在《性自命出》与毛诗“发乎情”的观点之间,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连结环节: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被认为是子思、孟子学派的代表性作品,而孟子的性情思想又主要发展了《性自命出》的“情”本观。而深入探讨孟子的情本观能够发现,孟子的性善说正是毛诗“发乎情”观点的直接导源。
比较孟子性情论中的“情”本思想和《诗序》中“发乎情”的思想脉络谱系能够发现,虽然两者一为哲学功能探讨,一为《诗》学价值描述,然而两者脉络谱系上的渊源关联却清晰可辨:孟子所描述的是以“情”为根源而生发出仁义之端,并继而影响至乐,最终外化至手舞足蹈的乐教结果的性情观进路。孟子的“情”本思想主要由三个重要元素构成:即“情”“乐”“舞”,然而这三种元素在《毛诗序》中也均有出现,其发展进路几乎与孟子的“情”本思想若合符契。两个在内在思想发展进路上的高度相似提醒我们,《毛诗序》“发乎情”的观点所体现的,正是自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至孟子性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情本观”, 孟子的“情”本思想正是《毛诗序》“发乎情”思想的直接导源。
由于汉《诗》的性情思想中影响最巨、泽被最远者,正是《毛诗序》“发乎情”的“情”本观,故而虽然仅取毛诗一端,但这也足以证明汉代《诗》学阐释对“情”的重视与孟子的“情”本思想之间密切的渊源关联。
从以上分析来看,汉代《诗》学重“情”的阐释理路,与荀子关系较浅而与孟子关联密切。由此可见,不仅汉代《诗》学的政治化、经学化阐释途径由孟子而开;汉代《诗》学对“情”的重视同样以孟子为导源。
(三)“四始”设置与“迹熄诗亡”:“四始”说对孟子《诗》学观的全然贯彻四家诗不仅在诗义阐释上与孟子解《诗》多有相合,在核心《诗》学体系的构建上也与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说密切相关:四家诗均不约而同地把《诗》对王道政教的承载作为《诗》义解读的第一要义。
鲁诗的“四始”说是鲁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的纲领性观点:“《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诗》的经学化意义正是由此得以初步确定的。鲁诗“四诗”的设置恰好对应了周代王道发展从开始、发展到鼎盛、衰落的四个关键阶段,这一设置意图恰恰与孟子的“迹熄诗亡”说若合符契,“迹熄诗亡”观也正是通过西周王道社会的发展阶段与《诗》的传播过程相对应,而确定了《诗》对王道制度的承载与依附关系。
齐诗的“四始”“五际”说在对孟子的承袭上也与鲁诗殊途同归,虽糅合了阴阳五行思想表现为“四始”“五际”:“《大明》在亥,水始;《四牡》在寅,木始;《嘉鱼》在巳,火始;《鸿雁》在申,金始”,但也同样是以具体《诗》篇对应王道盛衰的具体发展过程,以展现出其《诗》承载王道思想的核心意图。
尽管韩诗并没有“四始”说传世,然而《关雎》“为王道之原”的观点,也同样是以《诗》之首篇对应了王道社会发展的源头,其《诗》学意图与孟子以王道终结对应《诗》的传播终结的做法并无二致。
毛诗“《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也体现出与鲁、齐、韩三家诗相似的特点。此外,《诗序》对三十一篇《大雅》的旨意阐发恰恰对应了周朝初建至衰落的整个发展历史。《毛诗谱》的创作意图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根据《诗谱》中《诗》三百的时代分布频率可以发现,三百篇在整个王道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重点集中在几个时代:文王之世,成王之世,幽王时期和平、桓公时期,而这恰恰对应了关乎周朝王道制度发生重大转变的几个关键时期。郑玄《诗谱》的时代设置也再次集中体现了孟子的“迹熄诗亡”思想。
四家诗的核心价值体系,决定了汉代《诗》学的发展方向和整体发展路径,四家诗不约而同把“迹熄诗亡”说纳入各自核心价值体系的做法,不仅说明了四家诗对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的一致认同,也意味着四家诗对孟子《诗》学正传地位的高度认可与肯定。如果说荀子构成了四家诗释义的主要来源,那么孟子则与四家诗的核心《诗》学价值体系息息相关。
(四)“杂花生树”: 四家诗学者对孟子的多方蹈袭虽然四家诗学者均曾明确肯定了孟子与荀子善言《诗》的学术特点,然而打破就《诗》论《诗》的模式,从更广泛的学术发展角度来看,汉代四家诗与孟子关联也要比与荀子的关联更为深远和广泛。
其一,四家诗学者的著述风貌从孟子处获益匪浅。
首先,四家诗的《诗》学著述存在着承袭孟子的部分,例如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的做法源于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观的承袭;而郑玄的《毛诗传笺》和《毛诗谱》的创作源于对孟子“知人论世”和“迹熄诗亡”的贯彻。
其次,汉代研习四家诗的学者在其与《诗》没有明显牵涉的著作中,对孟子也多有蹈袭,其中尤其以司马迁的《史记》和赵岐的《孟子章句》表现最为明显:据史料记载司马迁所习为鲁诗,然而在《诗》之外,司马迁的《史记》在史料选择和创作意图上均受到了孟子的直接影响;同样的情况在赵岐身上也有出现,其注疏之作《孟子章句》打破了汉儒注疏的惯例,采用了“章别其指”的全新训释方式,即在每章末尾撰写章指,总括该章整体意义,标明孟子创作意旨。根据赵岐在《孟子章句》中的明文表述可知,这种冠以“章指”之名、在每章最后推求作者旨意的章指设置,正是其在注疏体例上对孟子“以意逆志”《诗》学观点的全然贯彻。
通过以上诸例可以明显看出,孟子对汉代四家诗的影响不仅限于《诗》之内部,而是已经渗入《诗》学之外,深深影响到了四家诗学者的著述风貌。这种重视,是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
其二,有汉一代,关于《孟子》的注疏之作出现了五部,且其中两部成于四家诗学者之手;与之相较,终汉一世,关于《荀子》的注疏没有出现一部,更无论出于四家诗学者之手的注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四家诗学者对孟、荀的不同重视程度。
此外,虽然汉代四家诗学者对荀子的《诗》学释义多有承袭,这也是判定荀子与四家诗渊源的主要依据;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四家诗在《诗》学阐释上,包括原文引用、诗旨相合、言语化用等诸多方面,对孟子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蹈袭与接续,甚至其征引的频率也远在荀子之外的先秦其他诸子之上。综上可见,虽然汉代四家诗在承袭孟子时表现各异,但其最终的指向却是一致的,即通过不同的角度对孟子《诗》学贡献的再三致意。
三、“荀皮孟骨”——汉代《诗》学渊源的一个合理解说
综上可见,汉代《诗》学的发展进程不仅具有“祖荀”特点,同时也有鲜明的“宗孟”倾向。
前贤之说不可遽废,荀子为汉诗渊源的观点绵延至今,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汉代四家诗的诗义承袭多与《荀子》相合即为明证。不过“宗孟”与“祖荀”这两种倾向却并不矛盾,二者虽然看似判若参商,实则异流同源,它们对汉代《诗》学的影响体现在不同层面上:就荀子而言,汉代《诗》学主要在诗义阐释上大量吸纳了荀子的观点,后人对荀子《诗》学正宗地位的判定也主要着眼于此;较之荀子,汉儒对孟子的诗义阐释似乎重视不足,然而深入探究汉代《诗》学的发展进程却会发现,孟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却是根本和深远的:汉代《诗》学的发展进程赖孟子而定;汉代四家诗的核心《诗》学价值均源于对孟子的承袭;四家诗的思想,包括阴阳五行、仁政、性情观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孟子的影响。汉代《诗》学发展进程中这种以荀子为体、以孟子为用,外在遵荀学、而内在遵孟学的现象,以“荀皮孟骨”名之或许才是对汉代《诗》学渊源问题的一个相对中肯的评价。
综上可见,孟子同样是影响汉代《诗》学发展至深至远的重要导源。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编:
审核:杨凯
责编:杨凯